发布时间:2024-02-18 22:32:41 浏览:
OB视讯癸卯大雪前夕,海宁档案馆吴忠建先生赠我刚出版的《百年图志一一海宁市档案馆老照片珍辑(精编版)》。这册一公斤多重的大开本画册,收入539幅展示近百年来,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浙江省海宁市的建设成果,给我以故乡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文明诸多方面的视觉印象。某些照片,特别是某些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,使我联想翩翩。
说句老实话,我对故乡海宁并不了解。我在斜桥长大,只到过硖石和盐官,只知道硖石天益兴的猪油酥糖和盐官海塘上的那只大铁牛。当然,还有斜桥榨菜,一直是我在杭州读书和在衢州工作的这半个多世纪中的骄傲。
1952年我从斜桥完小毕业,到杭州读完了初中和高中。1958年高中毕业后,就到衢州工作,在衢州呆了整整六十五年。然而,故乡却常现梦中。
当我看到《海宁县疏浚宁郭塘河施工情形》这幅摄于1947年4月1日的黑白照片,我居然想起了这一史实。那年我十岁,还小,但“开河”,每户人家要派一个大人挖几天河泥的事,我记得。我父亲是银匠,从未干过农活,他就请“洪年哥”,即我的大娘舅代他去挖了几天河泥,就完事了。
p59那两幅分别摄于1972年和1977年的《剥络麻》和《洗络麻》照片,就令我想起读小学五年级时的开荒地种络麻,以及此后每年暑假到舅舅家帮助剥络麻的往事。
先说种络麻。斜桥农村本无络麻,当局为了发展农业,从笕桥引进络麻,在海宁、崇德(1958年并入桐乡)一带种植。斜桥完小的老师和高年级学生,到学校南面臭水浜那片坟地里开荒种络麻。春种秋收,居然成功。我等同学还学会了剥络麻。两个人,一个人双手擒住络麻根部,另一个人拿两根尺把长、甜芦菽那么粗的细竹竿,将络麻杆夹住,顺势往一边拖到梢头。这样,络麻皮就被夹碎了,一下子就剥了下来,只剩下一根白亮湿润的络麻杆了。
读中学后,每年放暑假,我大多时间在舅舅家玩。剥络麻的日子,我也帮表哥打打下手(即擒住麻根)。
当时还没有环保意识,“洗络麻”,先要将剥下的络麻皮成捆扎好,浸在河浜里,十天半月,它的表皮腐烂了,再漂洗。漂洗也是力气活,人必须赤脚入水,双手捏住麻皮粗的一端,用力在水里左右甩洗。洗好再晾在竹竿上晒干,去收麻站出售。
1951年秋天,斜桥西环桥的河埠边水里出现了许多呆纯纯的老虾,成群昌条鱼与小鲫鱼聚集在水埠边张口闭口,像在喘气。这一怪事一下子传开了,好多小孩拿了竹篮、淘米箩,随便往水里兜一下,就能捞起不少鱼虾……第二年同样的季节,“发瘟”的鱼虾更多了,甚至有半死半活肚皮朝天的鲤鱼、草鱼顺水面躺下来——原来是“络麻水”作的孽!那时候,乡下的一些小河小浜里的水,都因浸洗络麻而变成了发臭的黑水、死水。
此后几十年,由于工厂排污,随意破坏生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重视环保,提倡“五水共治与设立“河长”,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,河水终于变清。不过,这是后线年的《硖石迎会提香拜香》,从图上看,这是“拜香”,是一种需要真本事,又肯受皮肉之苦的“艺术”一一表现者赤膊的背脊皮用穿棉线的钩子钩牢,棉线的另一端连在插在裤腰(前)带上的竹条上,再向下引,底端挂一串小灯笼,表演者走几步,拜一拜,如是往复OB视讯。“提香”更难,表演者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他们光着膀子,横伸右臂,臂上的皮下钩着十多只缝衣斜弯成的钩子。穿在针眼里的十多根丝线下端,吊着一只十多斤重的锡制香炉,臂下的皮肤被拉成倒三角形。走一程,歇一歇。护送的同伴在倒三角形的皮肤上喷一口烧酒,促使皮肤麻木并消炎。
小时候,我看见过“提香拜香,敬羡表演者的勇敢。这段记忆,我曾找到过文字资料:“凌家亭子庙会,斜桥云林庵俗称凌家亭子……每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举行庙会,会期三天,故事百堂(边走边表演故事近百个),行程三天累计百余里。”(《海宁县志》OB视讯。又,“1946年4月,镇郊农民发起迎神赛会,连续三天,耗法币近亿元,折合大米三千六百余石。”(《斜桥镇志》)
一石大米合120市斤。3600石,合432000斤。以现在米价1.4元一斤,60.48万元,也不是个小数目。老百姓愿意出这笔钱来“迎会”,说明虽经八年抗战,斜桥这个杭嘉湖平原上的鱼米之乡,老百姓的生活尚为富裕。
见p87海宁机床厂。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位已故友人虞自达。虞自达比我大二岁光景,祖籍义乌,生在硖石,在机床厂的前身通用机器厂当工人。1958年,他在某期《东海》上发表了一篇小说。他的小学同学,也是我的高中同学高健行,有一天领我到干河街他的家里,与他相识。高与我当时在杭州九中读书OB视讯。1956年,我俩高一(下)时,先后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儿童文学副刊”上登出过小诗。于是,我与虞自达一见如故。写小说比写诗歌难多了,我很敬佩他。不久,我又认得了高健行的另一位小学同学,1957年毕业于杭大中文系,在庆云中学当语文老师的严滨松。于是,爱好文学习作的三个硖石人和一个斜桥人,此后几十年中书信不断……这一切,就因为在通用机器厂做车工,以“工人虞自达署名(庄按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,刊载业余作者的作品,作者前面均标明身份,如列兵、工人、农民等)的一篇小说的“因缘”。
又如,p147斜桥火车站的两张照片。一张摄于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时。一张摄于20世纪80年代。斜桥火车站,我最熟悉不过了。我家就在火车站西南、隔着稻田的“横墙”与街道之间的元吉弄底。每趟火车开过,楼板也会轻轻震动。夜深人静时,连车站月台上小贩的喊叫声“粽子”“五香茶叶蛋”“瓜子花生”也听得到。
1952年我到杭州读中学和到衢州工作之后,半个多世纪在斜桥火车站上上下下,次数多的已记不清。
日军占领斜桥不久,就在火车站东、西两个洋桥(铁路桥)之间不到二公里的铁路沿线建了三座炮楼,以控制铁路。除车站西面黄墩港货运月台的炮楼已在解放初期拆毁外,车站票房东侧的炮楼和东洋桥北侧的师姑桥炮楼,依然完好,已成为斜桥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去年十月,朋友陪我到我从未去过的师姑桥炮楼考察,曾作文在《海宁档案史志》刊发,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斜桥、师姑桥据点杀害抗日战士与普通百姓的暴行。
诚如《百年图志》“前言”所说,“品读这些老照片,犹如在海宁的历史长廊中漫步,跟着一个个镜头穿越时空”,从而唤醒人们对已经消失或消失的乡土文明的记忆。
感谢故乡档案馆出这本书,感谢图片的搜集者和拍摄者。(癸卯年岁尾于骑塘桥旅舍)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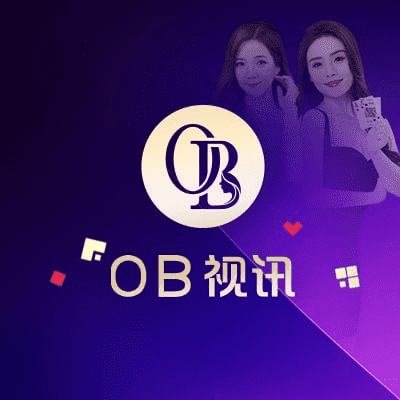







 公司新闻
公司新闻







